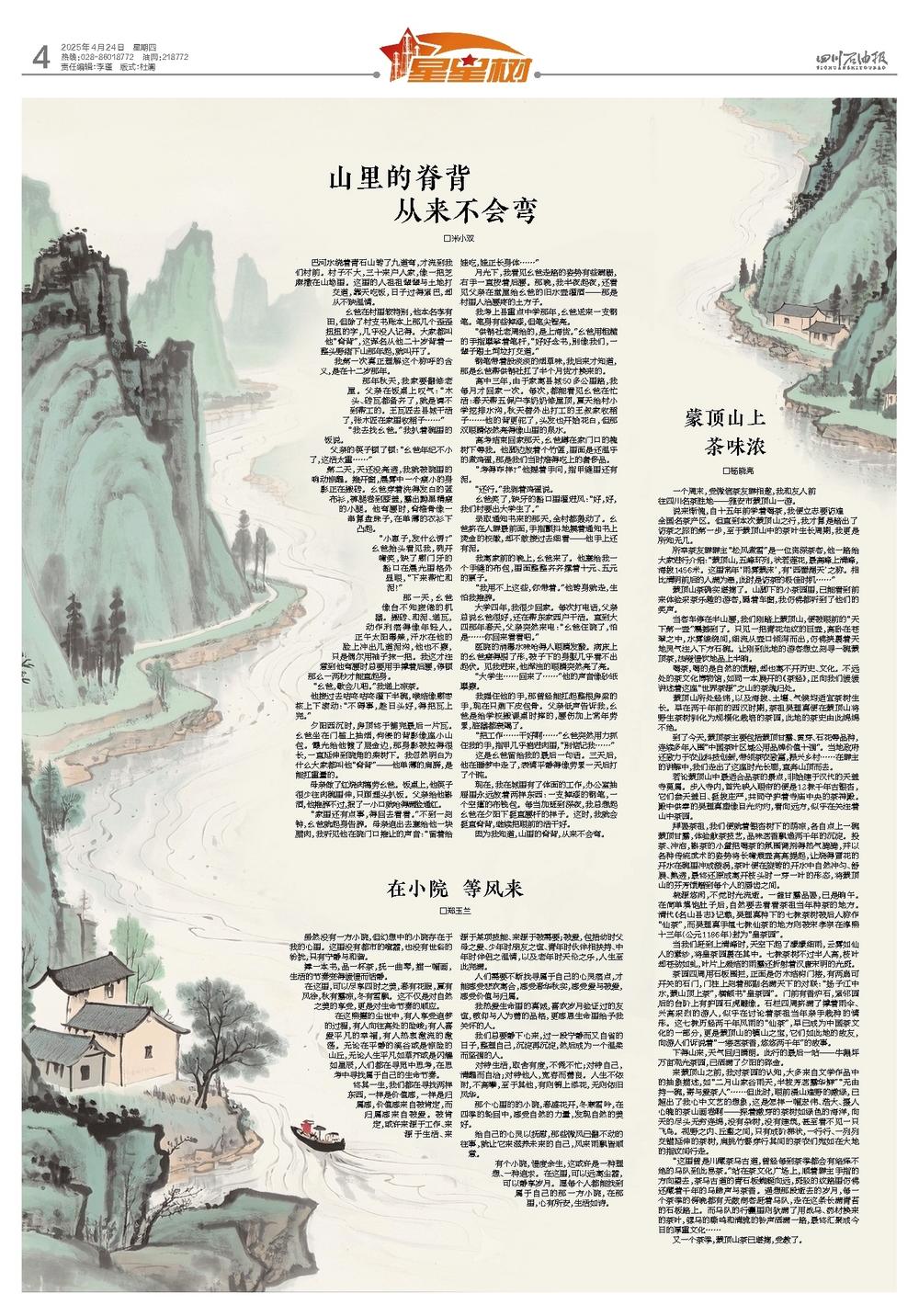□米小双
巴河水绕着青石山转了九道弯,才流到我们村前。村子不大,三十来户人家,像一把芝麻撒在山坳里。这里的人祖祖辈辈与土地打交道,靠天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却从不缺温情。
幺爸在村里较特别,他本名李有田,但除了村支书账本上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几乎没人记得。大家都叫他“脊背”,这诨名从他二十岁背着一整头野猪下山那年起,就叫开了。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这个称呼的含义,是在十二岁那年。
那年秋天,我家要翻修老屋。父亲在饭桌上叹气:“木头、砖瓦都备齐了,就是请不到帮工的。王瓦匠去县城干活了,张木匠在家里收稻子……”
“我去找幺爸。”我扒着碗里的饭说。
父亲的筷子顿了顿:“幺爸年纪不小了,这活太重……”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我就被院里的响动惊醒。推开窗,晨雾中一个瘦小的身影正在搬砖。幺爸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腿卷到膝盖,露出黝黑精瘦的小腿。他弯腰时,脊椎骨像一串算盘珠子,在单薄的衣衫下凸起。
“小崽子,发什么愣?”幺爸抬头看见我,咧开嘴笑,缺了颗门牙的豁口在晨光里格外显眼,“下来帮忙和泥!”
那一天,幺爸像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搬砖、和泥、递瓦,动作利落得像年轻人。正午太阳毒辣,汗水在他的脸上冲出几道泥沟,他也不擦,只是偶尔用袖子抹一把。我这才注意到他弯腰时总要用手撑着后腰,停顿那么一两秒才能直起身。
“幺爸,歇会儿吧。”我递上凉茶。
他接过去咕咚咕咚灌下半碗,喉结像颗枣核上下滚动:“不碍事,趁日头好,得把瓦上完。”
夕阳西沉时,房顶终于铺完最后一片瓦。幺爸坐在门槛上抽烟,佝偻的背影像座小山包。霞光给他镀了层金边,那身影被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院角的梨树下。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叫他“脊背”——他单薄的肩膀,是能扛重量的。
母亲做了红烧肉犒劳幺爸。饭桌上,他筷子很少往肉碗里伸,只顾埋头扒饭。父亲给他斟酒,他推辞不过,抿了一小口就呛得满脸通红。
“家里还有点事,得回去看看。”不到一刻钟,幺爸就起身告辞。母亲追出去塞给他一块腊肉,我听见他在院门口推让的声音:“留着给娃吃,娃正长身体……”
月光下,我看见幺爸走路的姿势有些蹒跚,右手一直按着后腰。那晚,我半夜起夜,还看见父亲在堂屋给幺爸的旧水壶灌酒——那是村里人治腰疼的土方子。
我考上县重点中学那年,幺爸送来一支钢笔。笔身有些掉漆,但笔尖锃亮。
“供销社老周给的,是上海货。”幺爸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笔杆,“好好念书,别像我们,一辈子跟土坷垃打交道。”
钢笔带着股淡淡的烟草味,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幺爸帮供销社扛了半个月货才换来的。
高中三年,由于家离县城50多公里路,我每月才回家一次。每次,都能看见幺爸在忙活:春天帮五保户李奶奶修屋顶,夏天给村小学挖排水沟,秋天替外出打工的王叔家收稻子……他的背更驼了,头发也开始花白,但那双眼睛依然亮得像山里的泉水。
高考结束回家那天,幺爸蹲在家门口的槐树下等我。他脚边放着个竹篮,里面是还温乎的煮鸡蛋,那是我们当时难得吃上的奢侈品。
“考得咋样?”他搓着手问,指甲缝里还有泥。
“还行。”我剥着鸡蛋说。
幺爸笑了,缺牙的豁口里灌进风:“好,好,我们村要出大学生了。”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全村都轰动了。幺爸挤在人群最前面,手指颤抖地摸着通知书上烫金的校徽,却不敢接过去细看——他手上还有泥。
我离家前的晚上,幺爸来了。他塞给我一个手缝的布包,里面整整齐齐摞着十元、五元的票子。
“我用不上这些,你带着。”他转身就走,生怕我推辞。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每次打电话,父亲总说幺爸很好,还在帮东家西户干活。直到大四那年春天,父亲突然来电:“幺爸住院了,怕是……你回来看看吧。”
医院的消毒水味呛得人眼睛发酸。病床上的幺爸瘦得脱了形,被子下的身躯几乎看不出起伏。见我进来,他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亮。
“大学生……回来了……”他的声音像砂纸摩擦。
我握住他的手,那曾经能扛起整根房梁的手,现在只剩下皮包骨。父亲低声告诉我,幺爸是给学校搬课桌时摔的,腰伤加上常年劳累,脏器都衰竭了。
“把工作……干好啊……”幺爸突然用力抓住我的手,指甲几乎掐进肉里,“别惦记我……”
这是幺爸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三天后,他在睡梦中走了,表情平静得像劳累一天后打了个盹。
现在,我在城里有了体面的工作,办公室抽屉里永远放着两样东西:一支掉漆的钢笔,一个空瘪的布钱包。每当加班到深夜,我总想起幺爸在夕阳下挺直腰杆的样子。这时,我就会挺直脊背,继续把眼前的活干好。
因为我知道,山里的脊背,从来不会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