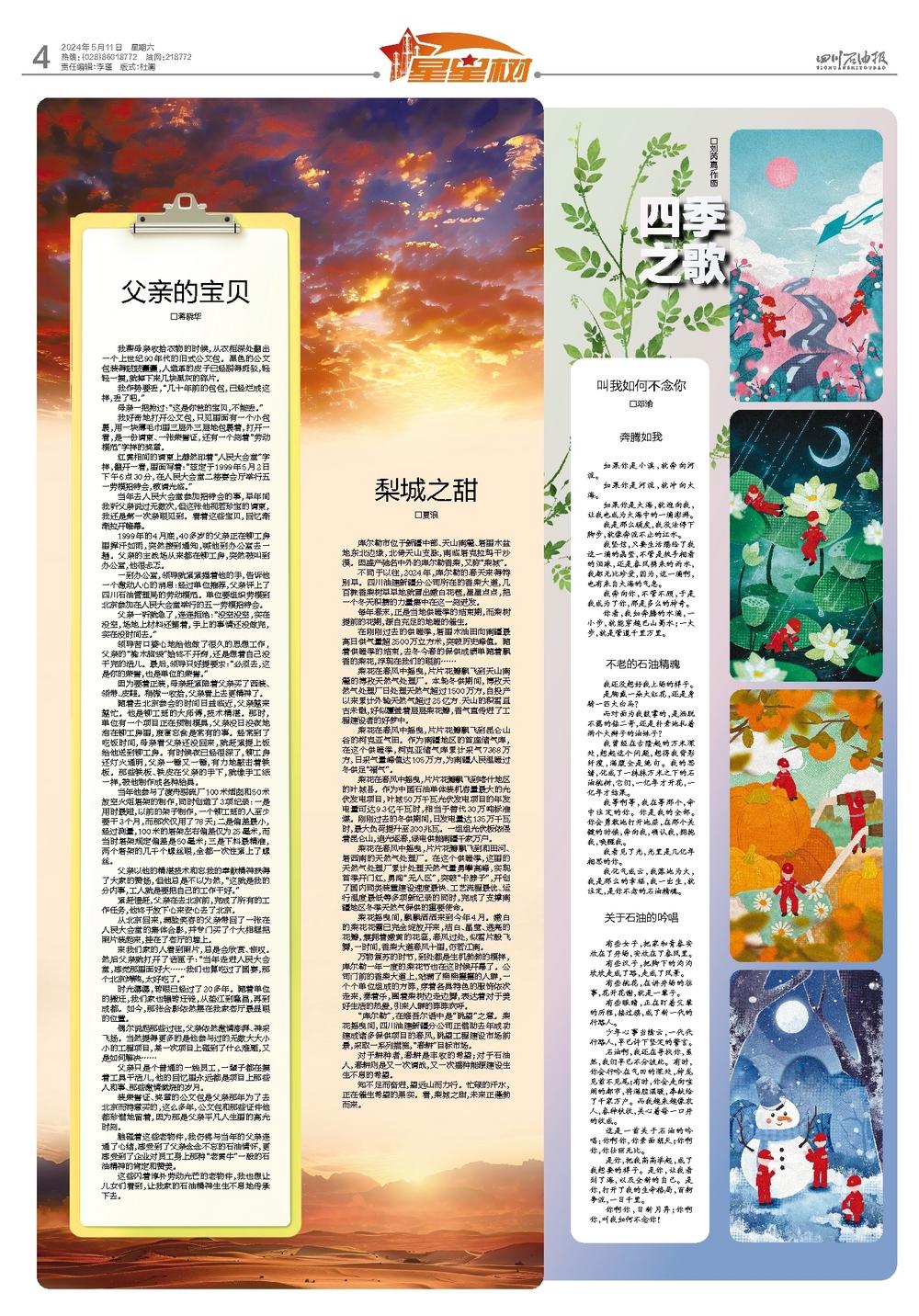□蒋晓华
我帮母亲收拾衣物的时候,从衣柜深处翻出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旧式公文包。黑色的公文包装得鼓鼓囊囊,人造革的皮子已经脱得斑驳,轻轻一摸,就掉下来几块黑灰的碎片。
我作势要丢,“几十年前的包包,已经烂成这样,丢了吧。”
母亲一把抢过:“这是你爸的宝贝,不能丢。”
我好奇地打开公文包,只见里面有一个小包裹,用一块薄毛巾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着,打开一看,是一份请柬、一张荣誉证,还有一个刻着“劳动模范”字样的奖章。
红黄相间的请柬上赫然印着“人民大会堂”字样,翻开一看,里面写着:“兹定于1999年5月2日下午6点30分,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举行五一劳模招待会,敬请光临。”
当年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招待会的事,早年间我听父亲说过无数次,但这张他视若珍宝的请柬,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看着这些宝贝,回忆渐渐拉开帷幕。
1999年的4月底,40多岁的父亲正在铆工房里挥汗如雨,突然接到通知,喊他到办公室去一趟。父亲的主战场从来都在铆工房,突然被叫到办公室,他很忐忑。
一到办公室,领导就紧紧握着他的手,告诉他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经过单位推荐,父亲评上了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劳动模范。单位要组织劳模到北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五一劳模招待会。
父亲一听就急了,连连拒绝:“没空没空,实在没空,场地上材料还铺着,手上的事情还没做完,实在没时间去。”
领导苦口婆心地给他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父亲的“榆木脑袋”始终不开窍,还是想着自己没干完的活儿。最后,领导只好提要求:“必须去,这是你的荣誉,也是单位的荣誉。”
因为要着正装,母亲赶紧陪着父亲买了西装、领带、皮鞋。稍微一收拾,父亲看上去更精神了。
随着去北京参会的时间日益临近,父亲越来越忙。他是铆工班的大师傅,技术精湛。那时,单位有一个项目正在预制模具,父亲没日没夜地泡在铆工房里,废寝忘食是常有的事。经常到了吃饭时间,母亲看父亲还没回来,就赶紧提上饭给他送到铆工房。有时候夜已经很深了,铆工房还灯火通明,父亲一锤又一锤,有力地敲击着铁板。那些铁板、铁皮在父亲的手下,就像手工纸一样,被他制作成各种胎具。
当年他参与了渡舟脱硫厂100米烟囱和50米放空火炬塔架的制作,同时创造了3项纪录:一是用时最短,以前的架子制作,一个铆工班的人至少要干3个月,而那次仅用了78天;二是偏差最小,经过测量,100米的塔架左右偏差仅为25毫米,而当时塔架规定偏差是50毫米;三是下料最精准,两个塔架的几千个螺丝眼,全都一次性紧上了螺丝。
父亲以他的精湛技术和忘我的奉献精神获得了大家的赞扬,但他总是不以为然,“这就是我的分内事,工人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干好。”
紧赶慢赶,父亲在去北京前,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任务,他终于放下心来安心去了北京。
从北京回来,满脸笑容的父亲带回了一张在人民大会堂的集体合影,并专门买了个大相框把照片装起来,挂在了客厅的墙上。
来我们家的人看到照片,总是会欣赏、惊叹。然后父亲就打开了话匣子:“当年走进人民大会堂,感觉那里面好大……我们也算吃过了国宴,那个北京烤鸭,太好吃了。”
时光潺潺,转眼已经过了20多年。随着单位的搬迁,我们家也辗转迁徙,从垫江到隆昌,再到成都。如今,那张合影依然摆在我家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偶尔说起那些过往,父亲依然激情澎湃、神采飞扬。当然提得更多的是他参与过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某一次项目上碰到了什么难题,又是如何解决……
父亲只是个普通的一线员工,一辈子都在摸着工具干活儿,他的回忆里永远都是项目上那些人和事、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装荣誉证、奖章的公文包是父亲那年为了去北京而特意买的,这么多年,公文包和那些证件他都珍惜地留着,因为那是父亲平凡人生里的高光时刻。
触碰着这些老物件,我仿佛与当年的父亲连通了心绪,感受到了父亲念念不忘的石油情怀,更感受到了企业对员工身上那种“老黄牛”一般的石油精神的肯定和赞美。
这些闪着淳朴劳动光芒的老物件,我也想让儿女们看到,让我家的石油精神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