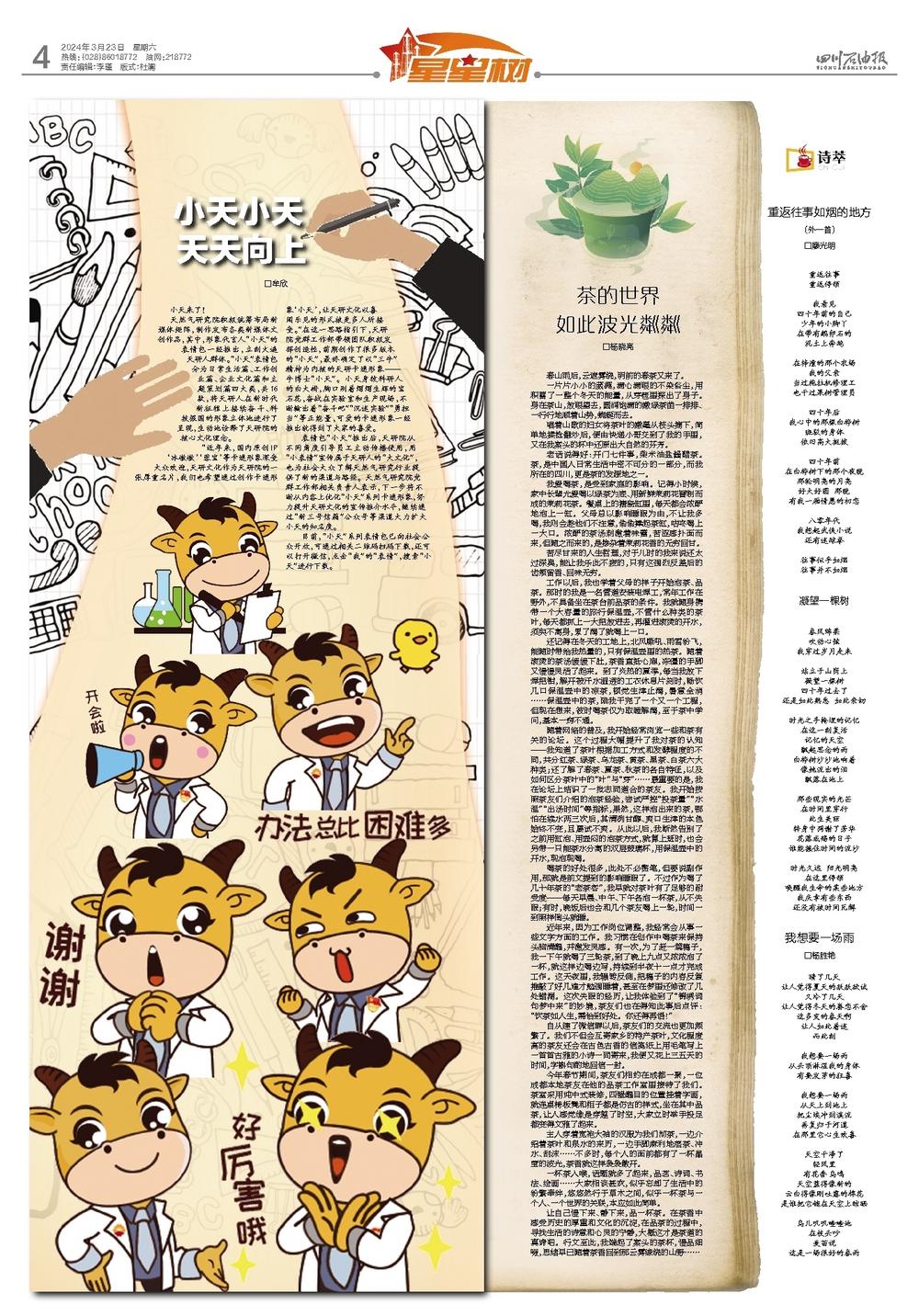□杨晓亮
春山雨后,云遮雾绕,明前的春茶又来了。
一片片小小的葳蕤,满心满眼的不染俗尘,用积蓄了一整个冬天的能量,从芽苞里探出了身子。身在茶山,放眼望去,圆润饱满的嫩绿茶苗一排排、一行行地顺着山势,蜿蜒而去。
唱着山歌的妇女将茶叶的嫩毫从枝头摘下,简单地揉捻翻炒后,便由快递小哥交到了我的手里,又在我案头的杯中还原出大自然的芬芳。
老话说得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我所在的四川,更是茶的发源地之一。
我爱喝茶,是受到家庭的影响。记得小时候,家中长辈尤爱喝以绿茶为底、用新鲜茉莉花窨制而成的茉莉花茶。餐桌上的搪瓷缸里,每天都会浓酽地泡上一缸。父母总以影响睡眠为由,不让我多喝,我则会趁他们不注意,偷偷捧起茶缸,咕咚喝上一大口。浓酽的茶汤刺激着味蕾,苦涩感扑面而来,但随之而来的,是掺杂着茉莉花香的无穷回甘。
苦尽甘来的人生哲理,对于儿时的我来说还太过深奥,能让我乐此不疲的,只有这强烈反差后的齿颊留香、回味无穷。
工作以后,我也学着父母的样子开始泡茶、品茶。那时的我是一名管道安装电焊工,常年工作在野外,不具备坐在茶台前品茶的条件。我就随身携带一个大容量的旅行保温壶,不管什么种类的茶叶,每天都抓上一大把放进去,再灌进滚烫的开水,须臾不离身,累了渴了就喝上一口。
还记得在冬天的工地上,北风嘶吼、雨雪纷飞,能随时带给我热量的,只有保温壶里的热茶。随着滚烫的茶汤缓缓下肚,茶香直抵心扉,冻僵的手脚又慢慢灵活了起来。到了炎热的夏季,每当我放下焊把钳,解开被汗水湿透的工衣休息片刻时,畅饮几口保温壶中的凉茶,顿觉生津止渴,暑意全消……保温壶中的茶,陪我干完了一个又一个工程,但现在想来,彼时喝茶仅为取暖解渴,至于茶中学问,基本一窍不通。
随着网络的普及,我开始经常浏览一些和茶有关的论坛。这个过程大幅提升了我对茶的认知——我知道了茶叶根据加工方式和发酵程度的不同,共分红茶、绿茶、乌龙茶、黄茶、黑茶、白茶六大种类;还了解了春茶、夏茶、秋茶的各自特征,以及如何区分茶叶中的“叶”与“芽”……最重要的是,我在论坛上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茶友。我开始按照茶友们介绍的泡茶经验,尝试严控“投茶量”“水温”“出汤时间”等指标,果然,这样泡出来的茶,哪怕在续水两三次后,其清冽甘醇、爽口生津的本色始终不变,且屡试不爽。从此以后,我断然告别了之前用缸泡、用壶闷的泡茶方式,就算上班时,也会另带一只能茶水分离的双层玻璃杯,用保温壶中的开水,现泡现喝。
喝茶的好处很多,此处不必赘笔,但要说副作用,那就是前文提到的影响睡眠了。不过作为喝了几十年茶的“老茶客”,我早就对茶叶有了足够的耐受度——每天早晨、中午、下午各泡一杯茶,从不失眠;有时,晚饭后也会和几个茶友喝上一轮,时间一到照样倒头就睡。
近年来,因为工作岗位调整,我经常会从事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我习惯在创作中喝茶来保持头脑清醒,并激发灵感。有一次,为了赶一篇稿子,我一下午就喝了三轮茶,到了晚上九点又浓浓泡了一杯,就这样边喝边写,持续到半夜十一点才完成工作。这天夜里,我辗转反侧,把稿子的内容反复推敲了好几遍才勉强睡着,甚至在梦里还修改了几处错漏。这次失眠的经历,让我体验到了“锦绣词句梦中来”的妙境,茶友们也在得知此事后点评:“饮茶如人生,需恰到好处。你还得再悟!”
自从建了微信群以后,茶友们的交流也更加频繁了。我们不但会互寄家乡的特产茶叶,文化程度高的茶友还会在古色古香的信笺纸上用毛笔写上一首首古雅的小诗一同寄来,我便又花上三五天的时间,字斟句酌地回信一封。
今年春节期间,茶友们相约在成都一聚,一位成都本地茶友在他的品茶工作室里接待了我们。茶室采用纯中式装修,四壁醒目的位置挂着字画,就连桌椅板凳和柜子都是仿古的样式,坐在其中品茶,让人感觉像是穿越了时空,大家立时举手投足都变得文雅了起来。
主人穿着宽袍大袖的汉服为我们沏茶,一边介绍着茶叶和泉水的来历,一边手脚麻利地落茶、冲水、刮沫……不多时,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了一杯晶莹的波光,茶香就这样袅袅散开。
一杯茶入喉,话题就多了起来,品茗、诗词、书法、绘画……大家相谈甚欢,似乎忘却了生活中的纷繁牵绊,悠悠然行于草木之间,似乎一杯茶与一个人、一个世界的关联,本应如此简单。
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品一杯茶。在茶香中感受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沉淀,在品茶的过程中,寻找生活的诗意和心灵的宁静,大概这才是茶道的真谛吧。行文至此,我端起了案头的茶杯,慢品细啜,思绪早已随着茶香回到那云雾缭绕的山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