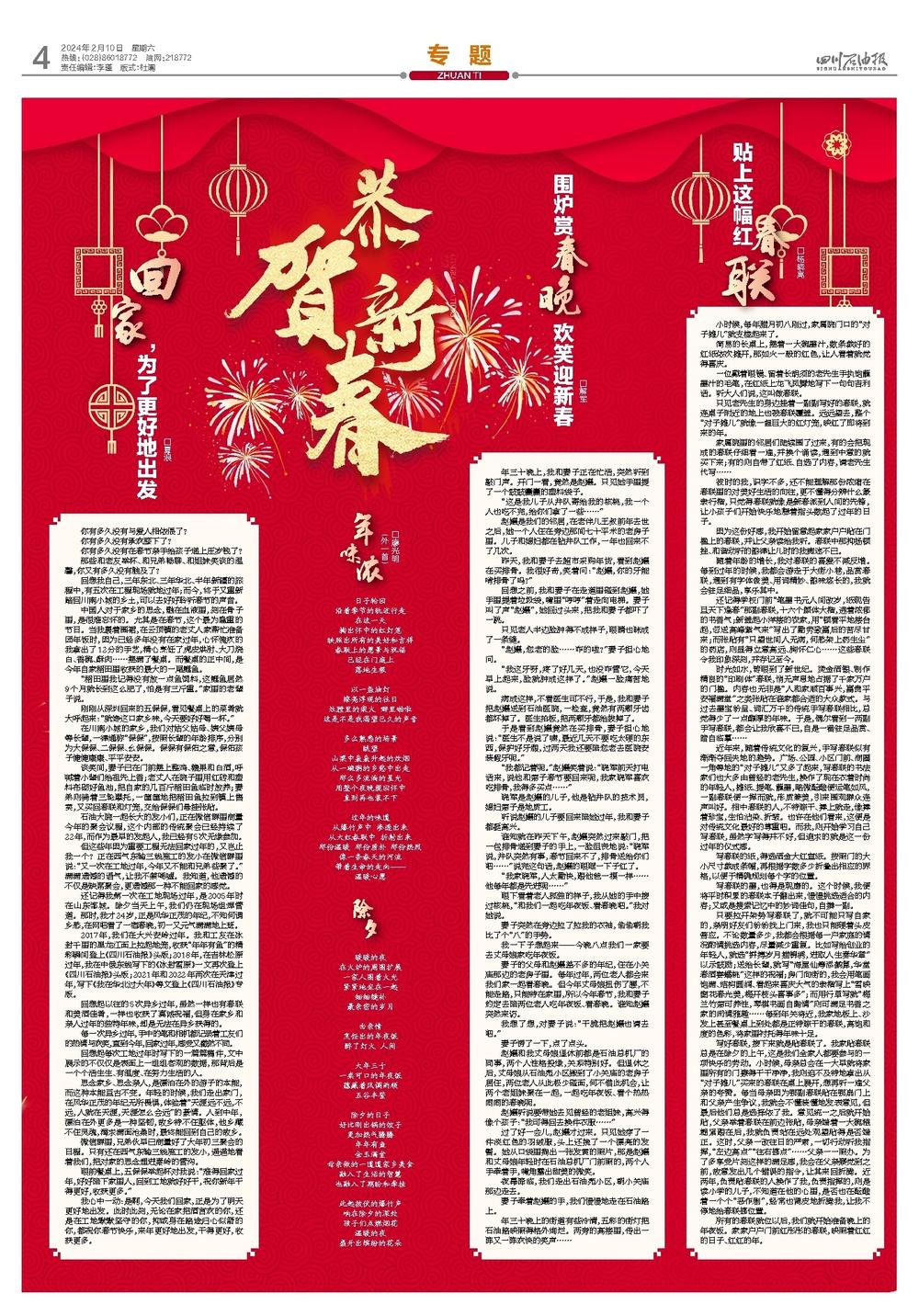□杨晓亮
小时候,每年腊月初八刚过,家属院门口的“对子摊儿”就支棱起来了。
简易的长桌上,摆着一大碗墨汁,数条裁好的红纸依次摊开,那如火一般的红色,让人看着就觉得喜庆。
一位戴着眼镜、留着长胡须的老先生手执饱蘸墨汁的毛笔,在红纸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一句句吉利话。听大人们说,这叫做春联。
只见老先生的身边挂着一副副写好的春联,就连桌子附近的地上也被春联覆盖。远远望去,整个“对子摊儿”就像一盏巨大的红灯笼,映红了即将到来的年。
家属院里的邻居们陆续围了过来,有的会把现成的春联仔细看一遍,并挨个诵读,遇到中意的就买下来;有的则自带了红纸、自选了内容,请老先生代写……
彼时的我,识字不多,还不能理解那份浓缩在春联里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不懂得分辨什么篆隶行楷,只觉得春联就像是新春派到人间的先锋,让小孩子们开始快乐地掰着指头数起了过年的日子。
因为这份好感,我开始留意起家家户户贴在门楹上的春联,并让父亲读给我听。春联中那抑扬顿挫、和谐动听的韵律让儿时的我痴迷不已。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春联的喜爱不减反增。每到过年的时候,我都会游走于大街小巷,品赏春联,遇到有字体俊美、用词精妙、韵味悠长的,我就会驻足细品,享乐其中。
还记得学校门前“笔墨书元人间改岁,纸砚告旦天下逢春”那副春联,十六个颜体大楷,透着浓郁的书香气;新盖起小洋楼的农家,用“顿看平地楼台起,忽送高峰紫气来”写出了勤劳致富后的苦尽甘来;而张贴有“只望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的药店,则显得立意高远、胸怀仁心……这些春联令我印象深刻,并存记至今。
时光如水,转眼到了新世纪。烫金洒银、制作精良的“印刷体”春联,悄无声息地占据了千家万户的门楹。内容也无非是“人和家顺百事兴,富贵平安福满堂”之类张贴在谁家都合适的大众款式。与过去墨宝纷呈、词汇万千的传统手写春联相比,总觉得少了一点醇厚的年味。于是,偶尔看到一两副手写春联,都会让我欣喜不已,自是一番驻足品赏、暗自临摹……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手写春联似有渐渐夺回失地的趋势。广场、公园、小区门前、商圈一角等地的“对子摊儿”又多了起来,写春联的书法家们也大多由曾经的老先生,换作了现在衣着时尚的年轻人,摊纸、提笔、蘸墨,略微酝酿便运笔如风,一副春联便一挥而就,形质兼美,引来围观群众连声叫好。相中春联的人,不待晾干、捧上就走,像捧着珍宝,生怕沾染、折皱。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便是对传统文化最好的尊重吧。而我,则开始学习自己写春联,虽然字写得并不好,但追求的就是这一份过年的仪式感。
写春联的纸,得选洒金大红宣纸。按照门的大小尺寸裁成条幅,再根据字数多少折叠出相应的界格,以便于精确规划每个字的位置。
写春联的墨,也得是现磨的。这个时候,我便将平时积累的春联本子翻出来,慢慢挑选适合的内容;又或是搜索记忆中的妙词佳句,自撰一副。
只要拉开架势写春联了,就不可能只写自家的,亲朋好友们纷纷找上门来,我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不论数量多少,我都会根据每一户家庭的情况酌情挑选内容,尽量减少重复。比如写给创业的年轻人,就选“拼搏岁月描锦绣,进取人生奏华章”以示鼓励;送给长辈,就写“海屋仙筹添鹤算,华堂春酒宴蟠桃”这样的祝福;房门向街的,我会用笔画饱满、结构圆润、看起来喜庆大气的隶楷写上“雪映窗花春光美,梅开枝头喜事多”;而用行草写就“梅兰竹菊可养性,琴棋书画自陶情”则可满足书香之家的闲情雅趣……每到年关将近,我家地板上、沙发上甚至餐桌上到处都是正待晾干的春联,高饱和度的色彩,将家里衬托得年味十足。
写好春联,接下来就是贴春联了。我家贴春联总是在除夕的上午,这是我们全家人都要参与的一项快乐的劳动。小时候,母亲总会在一大早就将家里所有的门擦得干干净净,我则迫不及待地拿出从“对子摊儿”买来的春联在桌上展开,想再听一遍父亲的夸赞。每当母亲因为哪副春联贴在哪扇门上和父亲产生争议,我就会不懂装懂地发表意见,但最后他们总是选择依了我。意见统一之后就开始贴,父亲举着春联在前边张贴,母亲端着一大碗糨糊紧跟在后,我就负责站在远处观望贴得是否端正。这时,父亲一改往日的严肃,一切行动听我指挥,“左边高点”“往右挪点”……父亲一一照办。为了多享受片刻这样的满足感,我会在父亲察觉到之前,故意发出几个错误的指令,让其来回折腾。近两年,负责贴春联的人换作了我,负责指挥的,则是读小学的儿子,不知道在他的心里,是否也在酝酿着一个个“恶作剧”,经常也调皮地折腾我,让我不停地给春联挪位置。
所有的春联就位以后,我们就开始准备晚上的年夜饭。家家户户门前红彤彤的春联,映照着红红的日子、红红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