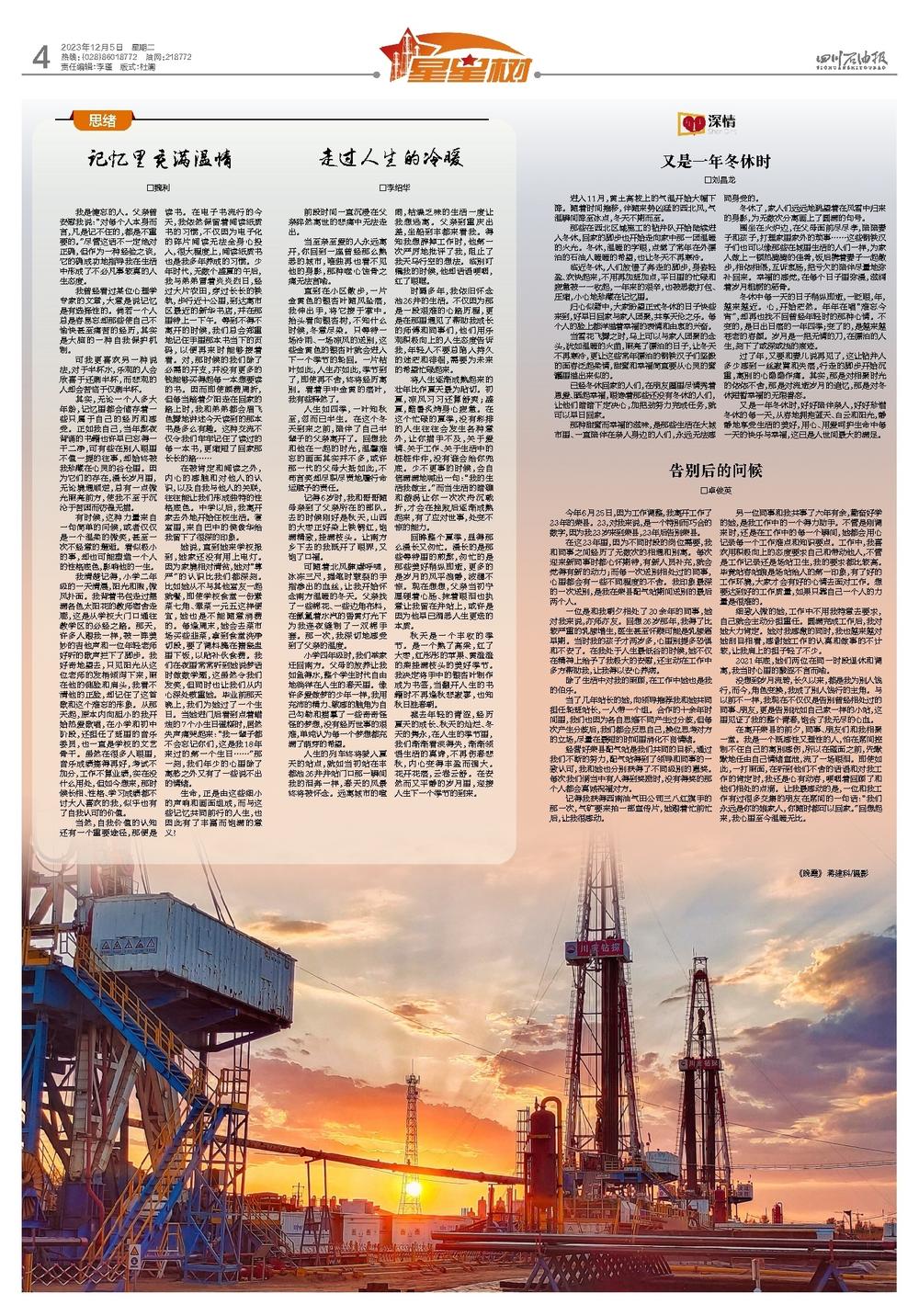□魏利
我是健忘的人。父亲曾安慰我说:“对每个人本身而言,凡是记不住的,都是不重要的。”尽管这话不一定绝对正确,但作为一种经验之谈,它的确成功地指导我在生活中形成了不必凡事较真的人生态度。
我曾经看过某位心理学专家的文章,大意是说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倘若一个人总是容易忘却那些使自己不愉快甚至痛苦的经历,其实是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可我更喜欢另一种说法,对于半杯水,乐观的人会欣喜于还剩半杯,而悲观的人却会苦恼于仅剩半杯。
其实,无论一个人多大年龄,记忆里都会储存着一些只属于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正如我自己,当年熬夜背诵的书籍也许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可有些在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往事,却始终被我珍藏在心灵的谷仓里。因为它们的存在,漫长岁月里,无论境遇顺逆,总有一点微光照亮前方,使我不至于沉沦于苦困而彷徨无措。
有时候,这种力量来自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者仅仅是一个温柔的微笑,甚至一次不经意的邂逅。看似极小的事,却也可能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底色,影响他的一生。
我清楚记得,小学二年级的一天清晨,阳光和煦,微风扑面。我背着书包走过摆满各色太阳花的教师宿舍走廊,这是从学校大门口通往教学区的必经之路。那天,许多人跟我一样,被一阵美妙的吉他声和一位年轻老师好听的歌声拦下了脚步。我好奇地望去,只见阳光从这位老师的发梢倾泻下来,照在他的侧脸和肩头,我看不清他的正脸,却记住了这首歌和这个难忘的形象。从那天起,原本内向胆小的我开始热爱歌唱,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还担任了班里的音乐委员,也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虽然在很多人眼里,音乐成绩搞得再好,考试不加分,工作不算业绩,实在没什么用处,但如今想来,那时候长相、性格、学习成绩都不讨大人喜欢的我,似乎也有了自我认可的价值。
当然,自我价值的认知还有一个重要途径,那便是读书。在电子书流行的今天,我依然保留着阅读纸质书的习惯,不仅因为电子化的碎片阅读无法全身心投入,很大程度上,阅读纸质书也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少年时代,无数个盛夏的午后,我与弟弟冒着炎炎烈日,经过大片农田,穿过长长的铁轨,步行近十公里,到达离市区最近的新华书店,并在那里待上一下午。等到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我们总会郑重地记住手里那本书当下的页码,以便再来时能够接着看。对,那时候的我们除了必需的开支,并没有更多的钱能够买得起每一本想要读的书。因而即使颇费周折,但每当踏着夕阳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和弟弟都会眉飞色舞地讲述今天读到的那本书是多么有趣。这种交流不仅令我们牢牢记住了读过的每一本书,更缩短了回家那长长的路……
在被肯定和阅读之外,内心的感触和对他人的认识,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关联,往往能让我们形成独特的性格底色。中学以后,我离开家去外地开始住校生活。寝室里,来自巴中的侯俊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她说,直到她来学校报到,她家还没有用上电灯。因为家境相对清贫,她对“尊严”的认识比我们都深刻。比如她从不与其他室友一起就餐,即使学校食堂一份素菜七角、荤菜一元五这样便宜,她也是不能随意消费的。每逢周末,她会去菜市场买些韭菜,拿到食堂洗净切段,要了调料腌在搪瓷盅里下饭,以贴补伙食费。我们在夜里常常听到她说梦话时做数学题,这虽然令我们发笑,但同时也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敬重她。毕业前那天晚上,我们为她过了一个生日。当她进门后看到点着蜡烛的7个小生日蛋糕时,居然失声痛哭起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这是我18年来过的第一个生日……”那一刻,我们年少的心里除了离愁之外又有了一些说不出的情绪。
生命,正是由这些细小的声响和画面组成,而与这些记忆共同前行的人生,也因此有了丰富而饱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