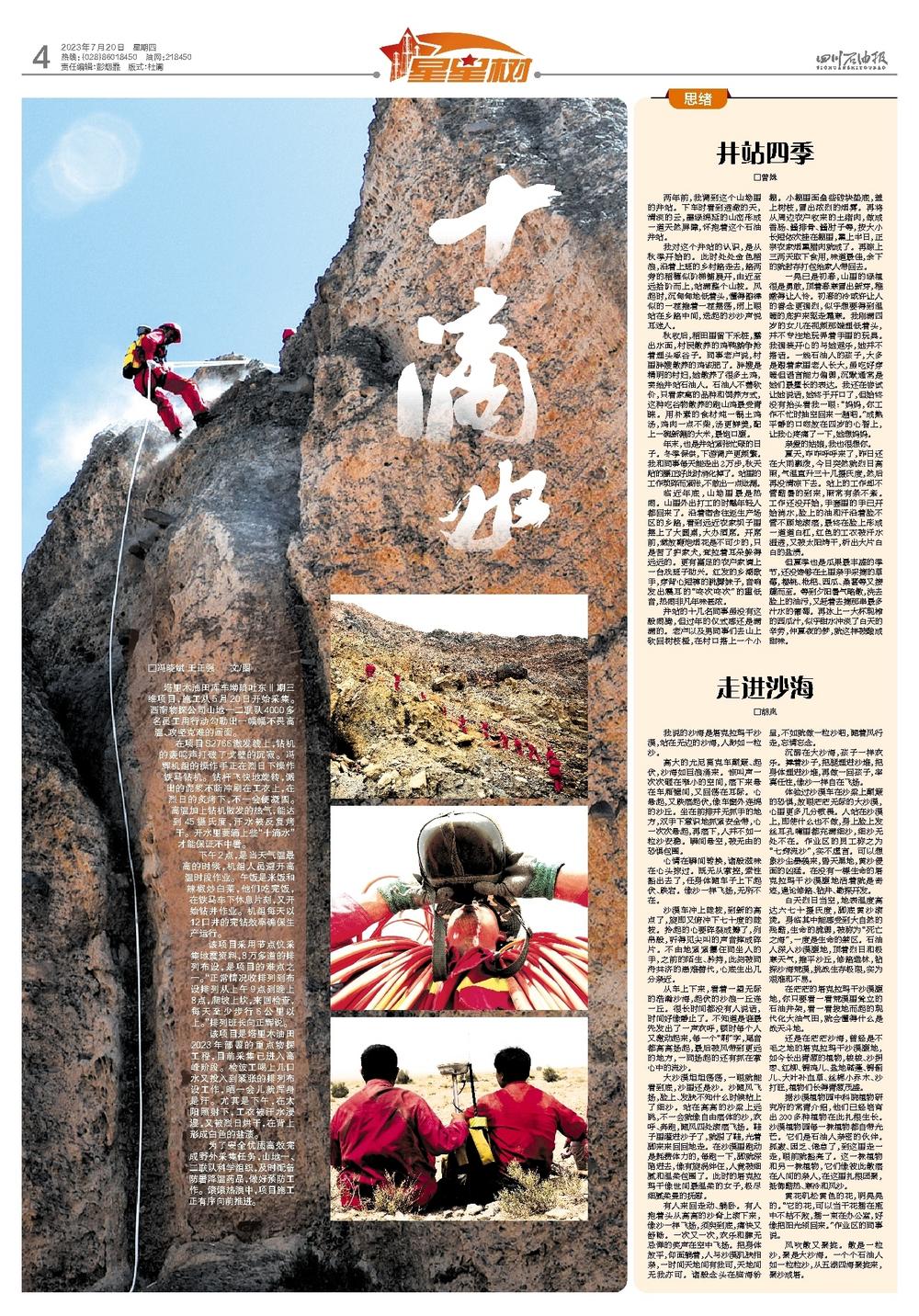□曾姝
两年前,我调到这个山坳里的井站。下车时看到透澈的天,清淡的云,墨绿绵延的山峦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怀抱着这个石油井站。
我对这个井站的认识,是从秋季开始的。此时处处金色稻浪,沿着上班的乡村路走去,路两旁的稻穗似阶梯铺展开,由近至远拾阶而上,站满整个山坡。风起时,沉甸甸地低着头,懂得韵律似的一茬推着一茬摆荡,闭上眼站在乡路中间,迭起的沙沙声悦耳迷人。
秋收后,稻田里留下禾桩,露出水面,村民散养的鸡鸭鹅争抢着埋头啄谷子。同事老卢说,村里胖嫂散养的鸡该肥了。胖嫂是精明的村妇,她散养了很多土鸡,卖给井站石油人。石油人不善砍价,只看家禽的品种和饲养方式,这种吃谷物散养的跑山鸡最受青睐。用朴素的食材炖一锅土鸡汤,鸡肉一点不柴,汤更鲜美,配上一碗新碾的大米,最饱口腹。
年末,也是井站紧张忙碌的日子。冬季保供,下游调产更频繁。我和同事每天能走出2万步,秋天贴的膘正好此时消化掉了。站里的工作琐碎而紧张,不敢出一点纰漏。
临近年底,山坳里最是热闹。山里外出打工的时髦年轻人都回来了。沿着宿舍往返生产场区的乡路,看到远近农家坝子里摆上了大圆桌,大办酒席。开席前,燃放鞭炮烟花是不可少的,只是苦了护家犬,耷拉着耳朵躲得远远的。更有富足的农户家请上一台戏班子助兴。红发的乡潮歌手,穿背心短裤的跳舞妹子,音响发出震耳的“咚次咚次”的重低音,热闹非凡年味甚浓。
井站的十几名同事虽没有这般闹腾,但过年的仪式感还是满满的。老卢以及男同事们去山上砍回树枝桠,在村口搭上一个小棚。小棚里面垒些砖块垫底,盖上树枝,冒出浓烈的烟雾。再将从周边农户收来的土猪肉,做成香肠、酱排骨、酱肘子等,按大小长短依次挂在棚里,熏上半日,正宗农家烟熏腊肉就成了。再晾上三两天取下食用,味道最佳,余下的就封存打包给家人带回去。
一晃已是初春,山里的绿植很是勇敢,顶着春寒冒出新芽,稚嫩得让人怜。初春的冷或许让人的眷念更强烈,似乎想要得到温暖的庇护来驱走霜寒。我刚满四岁的女儿在视频那端埋低着头,并不专注地玩弄着手里的玩具。我强装开心的与她逗乐,她并不搭话。一线石油人的孩子,大多是跟着家里老人长大,虽吃好穿暖但语言能力偏弱,沉默通常是她们最擅长的表达。我还在尝试让她说话,她终于开口了,但始终没有抬头看我一眼:“妈妈,你工作不忙时抽空回来一趟吧。”成熟平静的口吻放在四岁的心智上,让我心疼痛了一下,她想妈妈。
亲爱的姑娘,我也很想你。
夏天,咋咋呼呼来了,昨日还在大雨瓢泼,今日突然就烈日高照,气温直升三十几摄氏度,然后再没清凉下去。站上的工作却不管酷暑的到来,照常有条不紊。工作还没开始,手套里的手已开始淌水,脸上的油和汗沿着脸不管不顾地滚落,最终在脸上形成一道道白杠,红色的工衣被汗水湿透,又被太阳烤干,析出大片白白的盐渍。
但夏季也是瓜果最丰盛的季节,还没馋够在土里亲手采摘的草莓,樱桃、枇杷、西瓜、桑葚等又接踵而至。等到夕阳暑气略散,洗去脸上的油污,又赶着去摘那串最多汁水的葡萄。再冰上一大杯现榨的西瓜汁,似乎甜水冲淡了白天的辛劳,仲夏夜的梦,就这样被酿成甜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