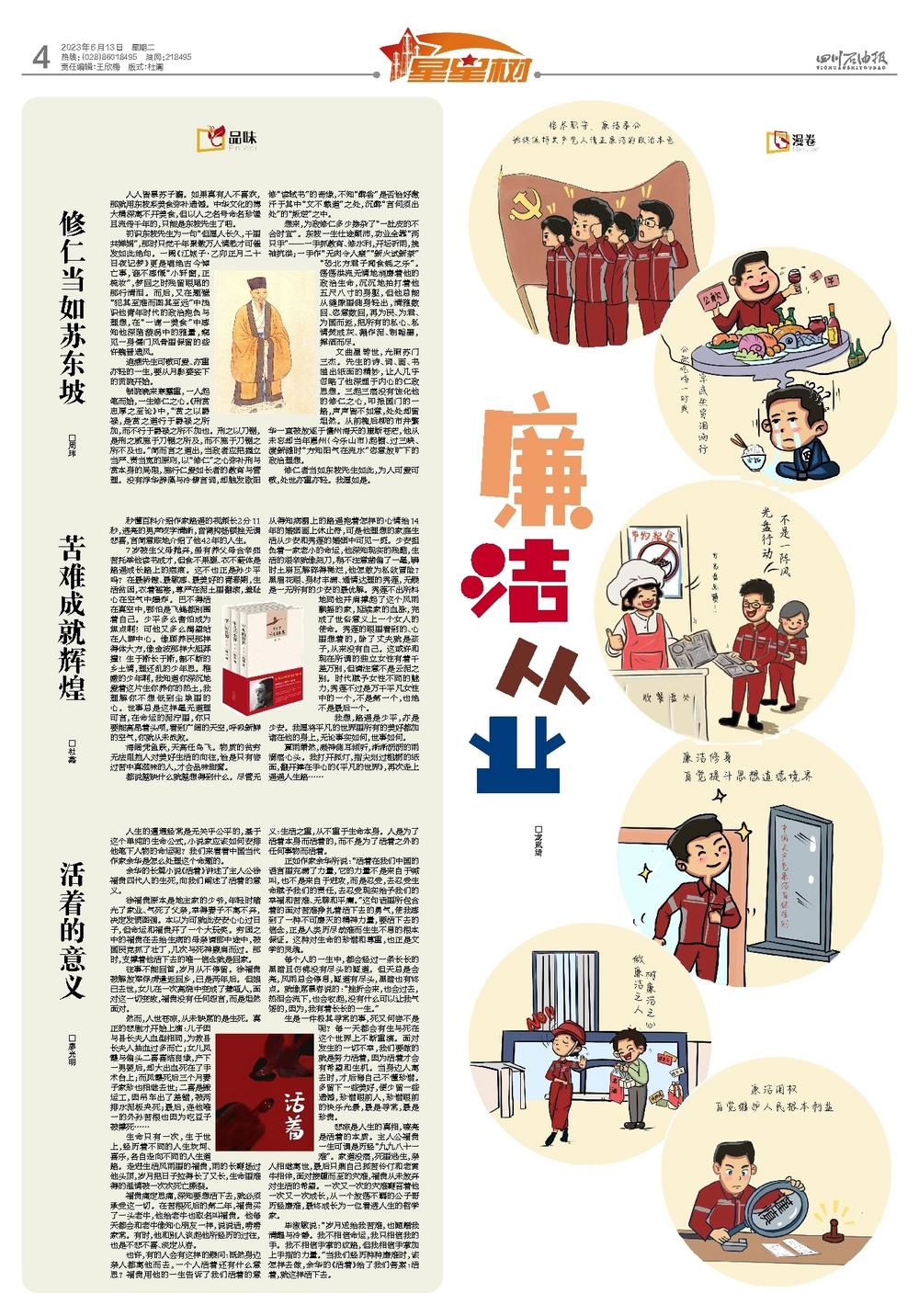□周玮
人人皆慕苏子瞻。如果真有人不喜欢,那就用东坡系美食弥补遗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美食,但以人之名号命名珍馐且流传千年的,只能是东坡先生了吧。
初识东坡先生为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时只觉千年聚散万人情愁才可催发如此绝句。一阙《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更是唱绝古今悼亡事,谁不感慨“小轩窗,正梳妆”,梦回之时残留眼尾的那行清泪。而后,又在题壁“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中浅识他青年时代的政治抱负与理想,在“一谪一美食”中感知他深陷漩涡中的雅量,窥见一身儒门风骨里保留的些许魏晋遗风。
追溯先生可敬可爱、亦重亦轻的一生,要从月影婆娑下的贡院开始。
锁院晚来寒露重,一人起笔而始,一生修仁之心。《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简而言之道出,当政者应把握立当严、责当宽的原则,以“修仁”之心弥补刑与赏本身的局限,施行仁爱如长者的教育与管理。没有浮华辞藻与冷僻言词,却触发欧阳修“读轼书”的奇缘,不知“醉翁”是否恰好激汗于其中“文不载道”之处,沉醉“言何须出处”的“叛逆”之中。
想来,为政修仁多少掺杂了“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东坡一生仕途颠沛,功业全靠“两只手”——一手抓教育、修水利,开坛祈雨,挽袖抗洪;一手作“无肉令人瘦”“新火试新茶”“恐北方君子闻食蚝之乐”。荡荡洪流无情地消磨着他的政治生命,沉沉地拍打着他五尺八寸的身躯,但他总能从缝隙里侧身轻出,清雅数回、恣意数回,再为民、为君、为国而返,把所有的私心、私情焚成灰、碾作泥、制翰墨,挥洒而尽。
文曲星转世,光照苏门三杰。先生的诗、词、画、书溢出纸面的精妙,让人几乎忽略了他深埋于内心的仁政思想。三起三落没有蚀化他的修仁之心,叩报国门的一路,声声皆不如意,处处却留坦然。从前槐后柳的市井繁华一直被放逐于儋州海天的崖断苍茫,他从未忘却当年嘉州(今乐山市)起锚、过三峡、渡新滩时“方知阳气在流水”恣意放旷下的政治理想。
修仁者当如东坡先生如此,为人可爱可敬,处世亦重亦轻。我愿如是。